1-1. 閱讀前請先了解預警內容哦~^
閱讀前請先了解預警內容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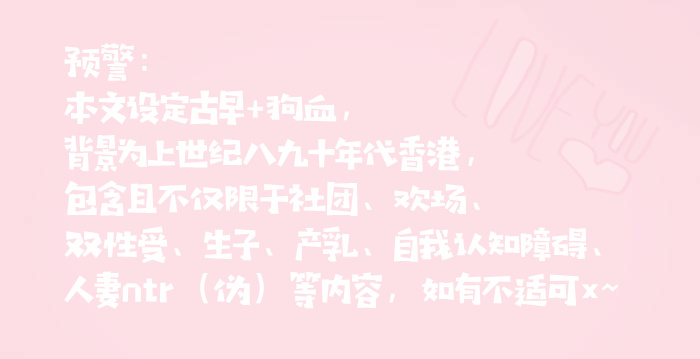
晚間的微雨帶來絲絲涼意,化作四下流淌於地面的豔麗霓虹。偶有車輪碾過街邊的水窪,揉碎映在其間的四個金紅大字——富麗舞廳。砵蘭街首屈一指的大型卡拉OK夜總會,今夜卻難得冷清了幾分,未如往日那樣滿是歡場常客、泊滿各色豪車。
擦得透亮的玻璃門內,兩名容貌姣好的女招待不時向外看去。而夜總會里,馬伕、媽咪和小姐們也已等足了一個小時,放到平日誰都不耐煩的情況,碰上包場這樣的好事便再無所謂,漫長的準備時間帶來的反倒是歡樂熱鬧的氣氛。
不過,這一切與陳寶祺無關。他獨自坐在最外面的角落,呆呆望著頭頂那盞灑出無數豔麗光斑的宇宙球燈,沉默地計算著與日加增的利息。
他甚至不敢再想自己的過去。
半個月前,母親勸他來港島打工,說是已經尋好一位同鄉幫忙打點,只要到了對岸就能進酒店做招待——其他親戚東拼西湊的錢很快被這位同鄉拿走,過來後陳寶祺又被對方以辦手續的名義索要了不菲的費用。帶在身邊的那些財物不夠打點關係,同鄉便讓“相熟的朋友”借了一些,再叫他在欠條上按了手印。
數日後,陳寶祺被直接送往婚姻註冊處。對方為他安排的“未婚夫”叫梁家明,因為有本地身份,只要與他登記結婚就可以長期居住。
陳寶祺從沒想到要以這樣的方式留下,雖感愕然,卻沒有其他辦法。他孤身一人來港,又是偷渡客的身份,首先考慮的不是與誰結婚的問題,而是怎樣維護這段虛假的婚姻讓自己不被遣返。
為了應付移民局的檢查,陳寶祺只能暫居在梁家明家,所剩不多的錢都用作房租。
陳寶祺曾一度寄希望於同鄉答應幫忙為自己介紹的那份工作,每天都想盡快還清欠他“朋友”那部分錢,再靠省吃儉用把工資寄回去補貼家裡。但他很快發現,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象的那樣美好,身邊的所有人一一撕下偽裝之後,他面對的是無數脅迫、威嚇和暴力。多年後,回憶初來港島的這段經歷,他仍感到深深的不安與恐懼。
原來,母親口中所謂好心人連帶他的朋友和梁家明三人都在蛇頭手下做事,先以同鄉的名義欺騙妙齡女性赴港,再用各種手段迫使她們簽下高利貸。梁家明這類提供配偶身份的姑爺仔既是監視者也是管理者,很快便將抱著賺錢願望的“大陸妹”們將按容貌優劣賣給不同的馬伕,再分至各大夜總會、歌舞廳、指壓、桑拿、酒吧等做妓女。直至深陷夜場,陳寶祺才知道,之前被他們帶來的人大多同自己一樣,靠全家四處借債才得到對方所說的工作機會,因此即使知道是上當受騙也再無退路,更不必說那些地方全部都有幫會背景,逃離的話不僅自己會遭到對方的報復和毆打,就連家人的安全也無法保證。
沒過幾日,陳寶祺就被上門要錢的打手搜走了傍身的少許餘財,他看不到任何出路,只能答應梁家明去舞廳做事。
說是做事,可兩人都清楚,是做皮肉生意。
但唯一出乎對方預料的是,陳寶祺不是女人。
或者說,他不是個完整的女人……也不是正常的男人。
得知陳寶祺的身上同時有著男人和女人的性徵,提前收下馬伕定金的梁家明簡直急怒攻心。他有賭博的習慣,前段時間去了澳門,為週轉手頭錢財便提前通知對方領人,也談定了日期送陳寶祺去接客。但現在的情況遠遠超出他的預料,手上的錢已輸個精光,要給對方的貨卻出了問題……他甚至想過把這波大腰細、上凸下翹的大陸妹多出的那根東西割掉當女人賣,只是時間實在太緊。要知道,每個馬欄背後都有幫會勢力,就算馬伕當街斬死他們這些從女人身上撈油水的姑爺仔都能找到頂罪的替身,可他的命只有一條。
起碼在下個貨物到手前,他必須得和陳寶祺一起保守這個秘密。
當然,富麗並不算只能看不能摸的金魚場,等到那時,後者下場如何都與他無關。
最終,梁家明以新來的人重感冒做藉口,請馬伕Andy暫將過夜陪睡改為陪酒。
Andy倒沒多心懷疑,因為他手上的女人太多,其中總有少數脾氣不好或惹到客人,又或者背了他聯繫其他馬伕轉場做事——陳寶祺這種願意聽話的大陸妹根本算不上問題,於是同意了梁家明的說法,讓他養幾天再做。
自此,陳寶祺就在富麗舞廳做事。
港島歡場大抵分作兩檔,一檔叫茶舞,每日下午兩點開始,做事的女仔多是中環白領或奢侈品銷售,靠一時的皮肉生意賺些外快補貼生活;另一檔叫晚舞,較前者傳統一些,客人也更多更雜,指的是各大夜場的公關小姐每夜九點到凌晨三點的坐檯時間。顯而易見,前者比後者檔次高上不少,來錢也快。
陳寶琪屬於後者間的下層,他廣東話說得一般,英文則是完全不懂,因此接到的生意極少,即使有客人看中他凹凸有致的身段,最終也會嫌陳寶祺不會歌舞木訥無趣而離開。場裡那些有權有勢的貴人輪不上趟,偶有感興趣的普通客人會被其他應召小姐搶去,儘管陳寶祺工作辛勞,生活狀況卻沒有任何改善,隔三差五還會被討債者追上門收走賺取的微薄錢財。
無奈的現狀與畸形的身體令他沉默寡言,而越是如此就越被其他舞女排擠,幾乎無法維持下去的生意幾乎將陳寶琪徹底推入了絕望的怪圈。
直到有一天,Andy將手下所有人叫到一起,滿面喜色地告訴她們明晚有老闆包場,大家都要盛裝出席作陪。場內眾人歡呼雀躍,包場意味著活少錢多,如果能傍上幾個有錢人,洋裝珠寶豪車也能收入囊中。
和其他光鮮亮麗的小姐不同,陳寶祺沒有華服香包也沒有高跟鞋,站在不起眼的角落裡,整個人彷彿是團空氣。散場後,唯一有些交情的阿芬在喊住了他,拽了拽陳寶祺那件花色過時的連衣裙,蹙眉道:“喂,又在發夢呀?Andy哥讓打扮得靚一點,你不會準備明天穿這個去吧。”
阿芬原也是看不起他的舞女之一,但數日前陳寶祺撿到她弄丟的耳環物歸原主,對方的態度好了很多,從先前的漠視轉為主動招呼,甚至幫他擺平了兩回小麻煩。雖然阿芬說話不太好聽,但陳寶祺卻能從中感受到幾分真心與關切,這反而是錢財之外他最需要的東西。
“我……沒有其他裙子。”
陳寶祺低下頭,目光滑到腳上那雙廉價的塑料涼鞋上。
他帶來的衣物全部老舊過時,沒有一件能穿進舞廳,就連身上這條都是之前與梁家明同居的女人留下的。
阿芬聞言蹙了蹙眉,道:“明天先去我那裡。機會難得,你長得不難看,波又足夠大,趁年輕搏一搏,總好過天天被她們笑。”
她頓了頓,又道:“我聽到Andy哥講電話,說明晚包場費六十六萬。寶祺,豁出去讓人玩幾次,要是被有錢佬看上,一年內賺多少都不成問題。”
“被人玩”會牽扯到身體的秘密,陳寶祺想都不敢想,不過阿芬提到的數字還是牽動著他脆弱的神經。
“六……六十六萬……”
六十六萬對陳寶琪來說是天價,但六萬則是他本週得還出的高利貸。催款者派來的打手都很懂行,不會和他的臉過不去,但留在後背、臀部和大腿上的傷痕絲毫不少。遭受毆打之後,他又因為沒錢買跌打藥,只能打些冷水敷在傷處緩解疼痛。
“我……我知道了。”
陳寶祺輕聲謝過阿芬,第二日去她住處試了衣服。因為胸部太大,提前準備好的兩套洋服都勒得很緊,最終只得換了條白色吊帶長裙。阿芬還替他稍稍敷些脂粉遮掩面色,再塗上一層口紅,讓人看上去不那麼平時那麼蒼白脆弱。
收整一番後,陳寶祺與她提前來到舞廳。
夜裡八點,Andy手下眾人進場,平日生意最好的幾個頭牌理所當然佔了中間,歧視鏈底端的“北姑”陳寶祺連舞池都沒能踏進去,直接被趕到外場看酒水臺。
阿芬掃了他一眼,搖搖頭。
直至十幾個衣衫華貴的客人進門,整個舞場迴盪著動聽的樂曲,陳寶祺才偷偷起身望了幾眼,可惜他的位置實在太遠,什麼都沒能看到。
歡歌、熱舞、酣飲一直持續到深夜,晚場的時間好像過得特別快,隨著客人陸續帶著應召女郎們離開,場內的小姐也各有去處。
見先前排擠他的幾人離了場,陳寶祺才恍恍惚惚地走到舒適一些的內場坐下。他小心翼翼地環顧四周,除了最中間的桌子還有三個男人在談話,其他卡座已經有服務生在清理杯盞。散場的氣氛讓他輕鬆下來,整個人癱在柔軟的椅子裡。
今天也沒有賺到錢……
阿芬好像早就走了,等會回去洗乾淨衣服……明天還給她吧。
正當陳寶祺託著腮思考還對方衣衫的時候,一個身著當下流行風格的皮衣青年從他身邊走過,幾秒後忽然停了腳步折返回來。
“……唔?”
他下意識往後縮了縮。
不等看清對方的臉,陳寶祺的胳膊被青年瞬間抓住,整個人跌跌撞撞地跟在他身後。
“來來來——”
青年一邊往中間走,一邊笑眯眯地對內場最後的客人招手,指著他高聲道:“蔣先生,這個怎麼樣,應該合你心意啦?”




